文/蒋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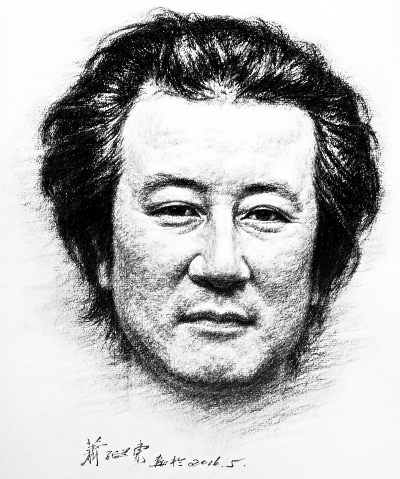
作者蒋蓝,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已出版《踪迹史》《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豹典》等多部文学、文化专著。
侠客的人与事,自然是出自文人的描摹。文人一方面感于时世艰难而彪炳异志,为此司马迁留下了《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另外一方面是寄托情怀,这有点类似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纸上抒情。文人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侠客许人,二是以侠客自许。其实不仅仅是“千古文人侠客梦”,而在于“侠客梦”淬就了我们的人格,并葆有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的侠从来就不是一门职业。侠起源于原始家族成员互助的古风,诞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大倡于晚清同盟会。现存史籍中,最早提到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最早论述到“侠客”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什么才能叫“轨于正义”?成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才叫“正义”吗?尽管价值观南辕北辙,但催生出侠客横空出世的条件出现了:一是社会的混乱和制度的黑暗,人间有太多灾难;二是一些人具有血性、良知和侠义气质,此为侠产生的主要因素。春秋战国遍布血与火,为“乱世天教重游侠”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舞台。
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就像一条条没有手柄的断刀,在全力递出去之后,就没有考虑收回。稳妥、保全、默生,绝对不是他们的事,那是儒生的事,是君子大人们的事。六人当中,只有专诸、聂政手刃了仇敌;要离、豫让则以空前的忠义感化了对手或圣灵,对手竟然自杀或暴亡成全了他们的失败;只有知识分子出身的荆轲、高渐离是彻底失意的,他们的利器在逼近秦始皇咽喉之际,命运使他们丧失了准头。某天,我突然恍悟到,这六人中,要离、豫让、聂政、高渐离四人先后毁容、自残,这犹如电光火石的一击,我似乎看到了蛰伏在他们的刀刃之后的,那比刀刃更为决绝的东西。
“侠义”绝不能被割裂。
“侠”本有通过武力挟持的意思,野草包含辅助之义;義字指羊,是“牺牲我像羊一样作为祭品”的意思。又因为“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義字从我。侠义之刃戛金断玉,响彻古中国的锈红色长空。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的推刃行为是一种自戕,竟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沉溺于“侠客梦”的人,知武而不知侠,慕侠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梁羽生曾指出:“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那么何为侠义呢?《墨子·经说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就是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以解别人之危,牺牲自己,扶危救困。纵观中国侠义史,可以发现墨、儒两家的侠义观最为接近,侠出于墨,这也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侠行的正义叙事。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认为:“实际上,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这一点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以‘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代为侠客的活动舞台。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是游侠之得以驰骋的特定时空。倘如此,则中国历史上得以产生侠客的时代远不止春秋至秦汉。”到了西汉,独裁者对自我利益的保护策略越发严密,严刑峻法广为实施,侠行逐渐式微,但一当铁幕露出缝隙,就会有侠士挺身而出,施展雷霆一击,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的古训。
甚至可以发现,面对一部洋洋《春秋》,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不妨可以总结为:复仇乃春秋之大义!在国家复仇与家族、血亲复仇之外,对陌生人一诺千金、拆骨为刀的侠义之举,才是跃升为复仇高音部的亮音。
因此,我也只能怀想,铺排侠客梦对我的招魂:
我无比缅怀先秦时代那种“独侠”的意象强力跃升为生与死的强悍主体。鲁迅先生认为,在王道文化所推崇的儒家恕道的“王土”之外,民间一直流淌着放血追义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葆有风骨、剔除杂质的生命活力,更是对正义的一次一次深犁。即使到了唐宋时期,侠义的文学是顶起旷大黑暗的一茎烛火。游侠俨然成为了黑暗时代的一抹亮色,作为先秦侠义的“剩余价值”,这是一个侠义逐渐式微的时代。晚清时节,同盟会·光复会先烈对腐败朝廷的铁血一击,是对远古侠义精神的一次大招魂。在辛亥革命前后,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五十多起。由“暗杀”到“明杀”的嬗变,展示了中国侠义精神的大纛,使彪炳千古的“暗杀时代”,彻底成为了轰天绝唱。
【编辑:袁毅】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