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劼(资深媒体人)
杨振宁回忆起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引了两句押韵打油诗调侃自己:
“If there is a bang,it is yang。”(哪里听到“梆”,哪里就有杨。)
诗里说的是,杨振宁初到美国,想从事实验物理,他在阿里森实验室呆了20个月。实验室有座加速器,脾气古怪,时常莫名其妙地漏气。实验室的人见怪不怪,哪里电路失常,不用多想,一脚踢上去,就好了。但杨振宁不在此列,只要他操作,必定惹得加速器老爷雷霆大发。
据说这两句诗是阿里森说开的,因此杨振宁还得了个“黄色危险品”的绰号。有了这样的教训,杨振宁彻底熄了搞实验的念头,一门心思专攻理论。
从物理学的代际来说,杨振宁的选择是必然也是无奈。
说必然,是因为现代物理学的一大标志就是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分野。所谓分野,指的是从此以后理论物理学家不可能从事实验工作,而实验物理学家也不可能从事理论工作。”从事“可能还是以职业而言,其实从学理而言,两者连互相理解都变得困难。用戴森的话说,理论物理学(爱因斯坦式)和实验物理学(卢瑟福式)其实代表了人类认知自然的两种范式:理论物理学相信宇宙的真理隐藏在数学之中,因此纯粹的思考就可以得到事实的真相;实验物理学家则认为物理学不是玩弄符号,而是发掘自然之真相。根据实验来了解自然,利用理论来解释实验才是物理之正途。因此两种范式都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同时以这两种范式来看世界,如同泡利的一个比喻,人能用左眼看清世界,也能用右眼看清世界,然而,同时睁开双眼,世界一片模糊。理论物理学家希望找出能解释任何事情的一般性原则,化大道为至简,简一分他们会高兴一分;实验物理学家则希望能找出事物的所有细节,他们喜爱宇宙的多样性,归大道于至繁,多复杂一分他们才会高兴一分。但大道不可能至简又至繁。
说无奈,是因为一旦选择了一种范式,必然舍弃另一种范式,而这种舍弃恰恰是对几百年来物理学传统的挽歌。物理学的真正诞生正是理论和实验紧密结合,将物理学从哲学的思辨、神学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早先的大师们也都是在理论、实验上,出此入彼,从容自如,比如伽利略、牛顿,都是典范。但到了现代,又各行其道,传统断绝。
实验与理论,必然的分野也罢,无奈的断绝也罢,总之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经如雷池不可逾越。用派斯在《玻尔传》里的说法,到了现代,实验活动和理论活动各自割据一方,划江而治,都已如此复杂庞大,能兼顾两者的物理学家或如恐龙一样灭绝了。杨振宁的导师费米就被誉为涉猎理论和实验两个领域的最后一只恐龙。最后之后,鱼和熊掌已然不可兼得。
为什么会如此?可能根本在于物理学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展到现代,在实验和理论领域已然各自极其复杂,实验从繁复的设计到浩大的工程到旷日持久的测试,理论从量子的极微极精到宇宙的极深极广,都远远超过了单个个体的智慧极限。真正应验了庄子之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单个的个体,顾得上脑,就顾不了手,想要两者兼顾,无异于痴人说梦。
理论之高山峨峨,实验之江河洋洋,志在高山者熙熙,志在江河者攘攘,而志在高山又志在江河者,斯人独憔悴。
后来杨振宁决定从芝加哥大学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去做博士后,临别费米不无惋惜地劝他,到那里至多呆一年,千万别太久。普高院的学术氛围太抽象,不利于年轻人从事实际工作。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理论和实验分野后,理论殿堂神一般的存在。在这里,除了脑,心手口都可以忽略不计,除了数学+理论物理,玄之又玄是形而上,其他实在、实验、实用等都是形而下,毫无兴趣。它建院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建实验室,爱因斯坦和外尔为此合说过一句名言:“在所生活的文明中有实验室就够了,所工作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不必非得有实验室。”
不仅不要实验室,等到奥本海默当院长,召集所有”头脑风暴“的大师们开会做了个决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不准从事任何与实验或应用有关的研究。
这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铁律:只准想,不准做,不准想做。充满了分手后的决绝。
费米极力拉住杨振宁想延续物理学的传统,可惜,这个传统在现在变成不可承受之重,费米的愿望变成绝唱。年轻人更向往的是纯理论领域里如奥本海默评价普高院的那些大神境界:”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的精英们在自我的世界里闪烁着无助的光芒。“
也许打油诗得续上两句:
听到了“梆”,就告别了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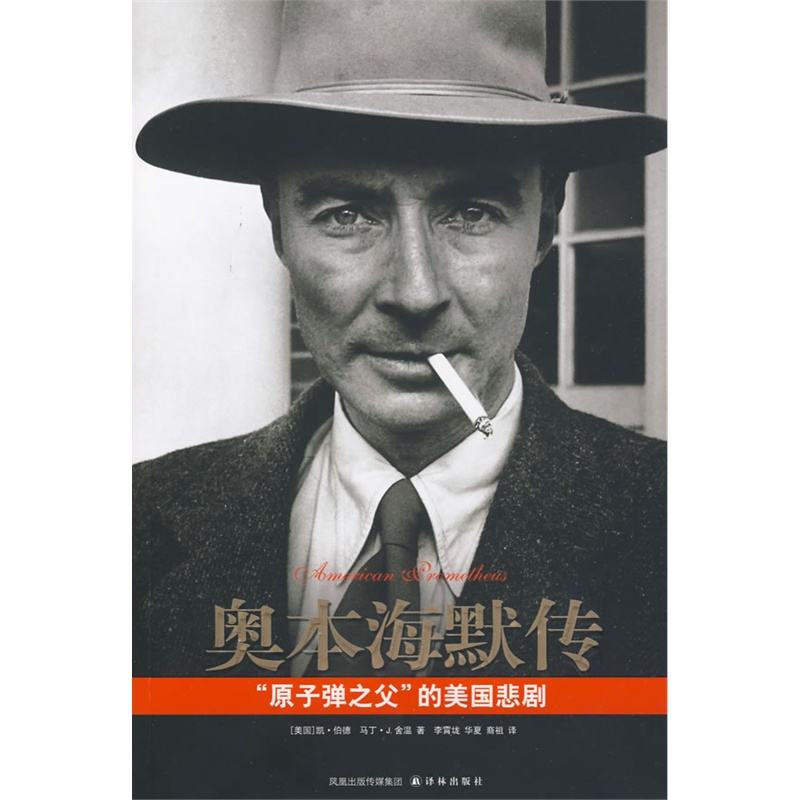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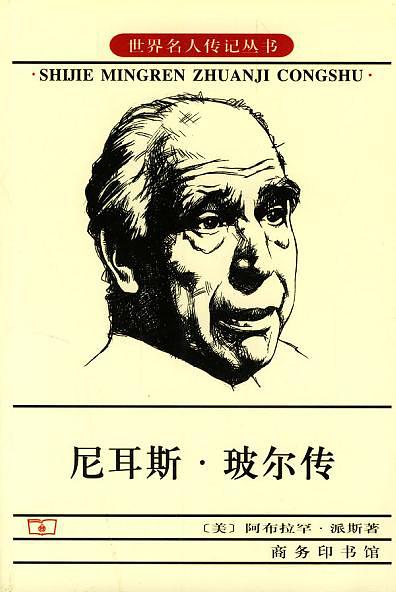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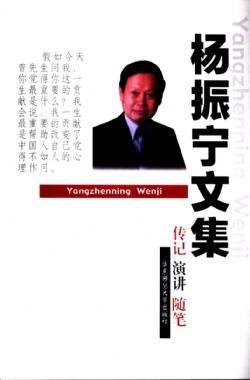
31
阅读书目:《杨振宁文集:传记演讲随笔》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凯•伯德/马丁•J.舍温 著 李霄垅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全方位的无限》 戴森 著 李笃中 译 三联书店
《尼耳斯•玻尔传》阿布拉罕•派斯 著 戈革 译 商务印书馆




请输入验证码